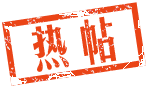醉酒驾驶必将产生严重后果,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它,这种行为将直接威胁到司机,行人和乘客的安全,但“醉驾入刑”多年来,社会评价褒贬不一,值得我们重新评估和深刻反思。
一、“醉驾入刑”引发的问题
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紧接着,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即“醉驾入刑”。
法律规范对醉驾标准、情节、道路认定等进行了完善的规定,规范实施以来,惩罚了大量“醉驾”犯罪人员。
(一) 醉驾入刑,扩大了打击面
“醉驾入刑”的覆盖面涉及到所有机动车驾驶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危险驾驶”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刑事案件,显示出62万多份判决;再以“醉酒驾驶”为关键词搜索,显示出53万多份刑事案件判决。
从2017年全国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来看,危险驾驶案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3.39%,其中86.03%的危险驾驶案件为醉驾案件。
由此可见,因“醉驾”而受到刑罚处罚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处罚对象数量庞大。
(二)刑法泛化一定程度激发矛盾
由于“醉驾入刑”后,处罚对象剧增。而我国对犯罪及其罪犯往往是作为“另类”对待的――罪犯本人打入另册,罪犯家属及其亲属一定程度被打上标签、给予区别对待,罪犯子女在升学、参军、公务员招考等方面受到审查、限制。
因此,划分出较大数量的“醉驾”罪犯,实质上映给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一定程度激化矛盾,扩大对立面。
(三)醉驾入刑相对粗糙,缺乏人文精神
《刑法》第十三条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醉酒驾驶”在刑法条文中属于“危险驾驶罪”,自然应受《刑法》第十三条之约束。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驾”行为,不管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一律认定为犯罪,并没有进行科学的梯度划分。
纵观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相对于抢劫罪等较轻。然而,在抢劫罪的辩护中尚可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而对“危险驾驶”案件却不认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法定条件,这对“醉驾入刑”者而言,似有不公平之疑虑。
(四)司法解释有所重视但非常有限
我国目前法律规定对于“醉驾”一律入刑,但《最高人民法院补充八种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
由于最高法对此条规定中的“情节显著轻微且危害不大”应如何适用,未做明确的解释。致使各地法院在具体司法审判中缺乏指导,司法实践中引用较少――大部分“醉驾”者虽有悔过的意识,但法律不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二、修改“醉驾入刑”的政策建议
(一)评估酒驾入刑科学性和适当性
“醉驾入刑”七年来,该条法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惩治犯罪,遏制“醉驾”的效果。但对较大比率的人群进行了刑事处罚,到底其法律效果如何,有待商榷:是可以降低刑事“威胁”,采用行政处罚“威胁”就可以达致规制交通的法律效果,还是目前的“醉驾”刑事处罚规定的确必须且恰当?
“醉驾”是否罚当其过、法当其罪?对“醉驾入刑”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立法、司法后评估,对数量庞大的人和车运行管理秩序,探索科学合理的设计管控方式,减少暴力管控措施,降低社会戾气,是法治建设深化细化科学化的应然步骤。
(二)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细化酒驾入刑标准
“醉驾”处罚门槛低,凡是“醉驾”一律入刑,最低处罚为拘役一月。一旦“醉驾”者被查到“醉酒驾驶”机动车,不考虑“醉驾”者的意识状态、行车速度、以及是否造成实际损害等因素,均被判处拘役刑以上。
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地方法院对“醉驾”处罚中的拘役采取缓刑来减轻处罚,但只做到了免其刑罚而没做到免其罪名。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中规定了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起点,提出对醉驾者的处罚应根据醉驾者的综合情况而定。因为指导意见属于法院内部指导性文件,法院在进行审判时可以将指导意见作为参考,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因此,为了确保刑罚对“醉驾”的精准惩罚,杜绝量刑的模糊化,还应明确醉驾中“情节显著轻微”状态的实际操作标准。
2017年1月,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相继规定了部分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醉驾”行为,使刑事处罚更符合法治规范。
(三)酒驾增加行政处罚,降低刑事处罚
对社会主体进行刑事处罚是社会管控中最严厉的惩治,没有更重的社会管控方式,故刑事处罚手段一定要慎重。能够采取其他较为温和的行政处罚措施达致控制社会危害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刑事处罚的适用。
对现有认定的“醉驾”进行分流,大部分采用行政处罚,乃至严重行政处罚,如拘留,较长时间拘留等方式进行处罚;少量的(如10%左右)的醉驾继续进行刑事处罚、惩罚高危险行为,降低社会整体危害程度,也减轻社会的戾气。
(四)探查处罚新手段实行处罚组合化
刑罚最终目的还是教育罪犯改正恶习,杜绝再犯。刑罚是靠限制人身自由来达到震慑作用,但其并不能直接改变罪犯的习惯。
对于“醉驾”情节轻微的醉酒者而言,连续的社会服务惩罚相对于刑罚而言,能够体现法律劝人为善的立法目的。
据浙江省新闻报道,浙江瑞安一名醉驾车主通过完成30多个小时的社会服务,被检察机关免于提起诉讼。
结合我国社区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刑罚轻型化改革的推进,“醉驾”行为根据其情节程度实行不同的处罚手段指日可待。
酒驾、醉驾处罚形式多样化。我国正在构建与完善个人与社会的信用体系,个人信用将对医疗、保险、出行以及社会福利等产生影响。可以采取行政处罚与降低信用积分的方式对酒驾人员进行处罚,醉驾人员可根据行为情节轻重来相应的降低信用积分,并记入信用档案。
酒驾、醉驾人员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可以对其作出“禁止令”,进而减少限制人身自由刑罚的使用。